(资讯)关注同志 《华商报》对同志生活的详细采访
点击次数:
本站发表: 2005-10-9 00:00
最后编辑: 景致
最后编辑: 2007-02-4 00:13
原载: http://news.huash.com/gb/news/2005-10/07/content_2269576.htm
本站发表: 2005-10-9 00:00
最后编辑: 景致
最后编辑: 2007-02-4 00:13
原载: http://news.huash.com/gb/news/2005-10/07/content_2269576.htm
阅读推荐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啦!!!
宋体; 为了解男性人群对尖锐湿疣疫苗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我们拟对男性人群展开此项调查,以为开展后期的尖锐湿疣疫苗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本次调查,我们需要了解您的一般情况及对尖锐湿疣疫苗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全程采用匿名形式。调查不会对您的健康和隐私造成伤害,同时我们保证对调查中所有可能涉及到您个人隐私的问题,给予严格保密。
用手机扫描下面二维码就可以领取红包啦!!!
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啦!!!
宋体; 为了解男性人群对尖锐湿疣疫苗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我们拟对男性人群展开此项调查,以为开展后期的尖锐湿疣疫苗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本次调查,我们需要了解您的一般情况及对尖锐湿疣疫苗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全程采用匿名形式。调查不会对您的健康和隐私造成伤害,同时我们保证对调查中所有可能涉及到您个人隐私的问题,给予严格保密。
用手机扫描下面二维码就可以领取红包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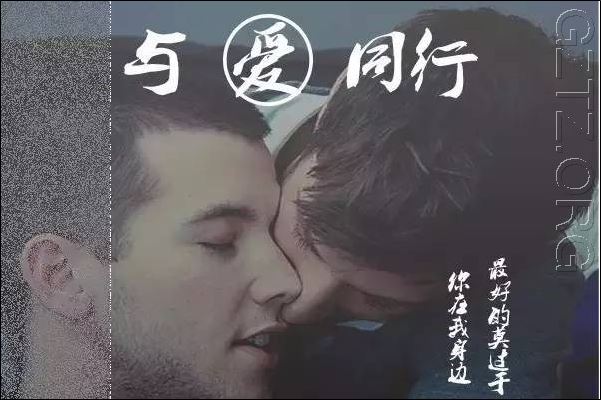 活动:与爱同行
活动:与爱同行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谈起性和健康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的“SEX-HEALTH图片大赛”正火热举行中哦!
谈起性和健康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的“SEX-HEALTH图片大赛”正火热举行中哦!
把你的想法注入到照片,图画,设计(图片或文字)与我们分享吧!
本次大赛将会给大赛前三名颁发奖励(第一名的奖励是iphone6一台,第二,三名将会有惊喜奖品)!
想了解详情请点击http://www.seshglobal.org/sex-health 《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8月初的一天,深圳连降暴雨,但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内却是人头攒动。来自香港的张锦雄Ken仔(以下简称Ken仔)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发表演讲。倘若不是Ken仔自曝,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是个艾滋病人,并在18年前因此而濒临死亡。
《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8月初的一天,深圳连降暴雨,但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内却是人头攒动。来自香港的张锦雄Ken仔(以下简称Ken仔)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发表演讲。倘若不是Ken仔自曝,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是个艾滋病人,并在18年前因此而濒临死亡。
栏目更新
- 2015-12-04青年学生染艾调查 男同性恋无套性交成传播主因
- 2015-12-04抗艾需消除同性恋者双重污名
- 2015-08-18美媒:北京东单公园为男同性恋提供安全港湾
- 2015-08-18高校教材“污名”同性恋 女生起诉获立案
- 2014-11-29【资讯】美国同性恋约炮应用Grindr的赚钱之道:寻找一夜情
- 2014-11-20【资讯】美男被性侵不愿公开 志愿者想帮忙遭拒
- 2014-11-17【资讯】广东梅毒、淋病患者去年报告数全国第一
- 2014-10-31【资讯】苹果CEO库克:身为同性恋者我感到很自豪
- 2014-10-31【资讯】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读库克的出柜文章
- 2014-10-29【资讯】台湾举行大规模同性恋游行,6.5万人参加
- 2014-10-11【资讯】爱沙尼亚通过同性恋婚姻法 允许同性恋领养小孩
- 2014-07-05【资讯】蔡明亮出书承认同性恋 自曝曾在外地猎艳
关注同志
《华商报》对同志生活的详细采访
(作者或来源) 华商报 ■2005年8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以生命的名义》,对话同性恋者。北京某高校大学生大玮(化名)以真实面貌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经历。节目还采访了其他几位同性恋者,以及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等数位从事同性恋者有关问题研究的人员。节目正视并尊重同性恋人群,并提出同性恋者作为社会一分子,在自我生活状态下应注意远离高危行为。■2005年9月29日,《南方周末》发表《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一文,文中受访者成都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冬称“这对伴侣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同性恋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积极面对生活。选择这样的生活需要很大的勇气,还需要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技巧。不要悲观地去想一切都不可能,其实一切都是可能的。有时不是自由度不够,而是我们不敢去想、不敢去做。”
同时,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江华称,实际上,同性恋者中有一大半人不管现状如何,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分享内心的渴望,不想孤单地吃饭、看电视、睡觉,异性恋者也无非如此。对于愿意缔结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关系的人,社会应该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证。同性恋者是社会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贡献的公民,为何要漠视他们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呢?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同性恋者都必须去结婚。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当你想要的时候,它应该在那儿。
落在这座城市里的阳光,也落在他们身上。但生活中,他们的情感,他们的选择,却注定要暗无天日。
他们全部的“罪恶”在于———他们是男人,却不爱女人;她们是女人,却排斥男人。违背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常规伦理,他们选择爱自己的同性。
他们中有公务员,有白领,有高学历者,也有工人、农民,打工的青年。在人群中,他们的比例是2%-5%。他们被称作同性恋者。
作家王小波曾在《他们的世界》一书中说: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
所以,我们走近了这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人群。同时发现,宽容,不仅是为他们,原来也是为我们自己。
“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希望找到我的另一半,而他是个男人。”这是夏桐从来不敢对人启齿的梦想。晚上8点,夏桐如约而至。此前的几天,我们在QQ上聊天,被他一次次地逼问:“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人群?”
我们在位于西安东郊的一所大学旁边见面。他比照片上显得更清瘦一些。衬衣是浅浅的黄,白色的休闲裤、运动鞋,短发精心地打理过了。看上去是个清爽、精明的大男孩。
夏桐,男,29岁,大学毕业。从外地来西安生活5年,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西北地区销售主管。他工作出色,与同事相处融洽,身边常有漂亮的女孩,他也努力表现出自己喜欢她们。然而,他却是个真正的Gay(男同性恋者的英文缩写)。
“如果我们这个人群,有一天能站起来,肯定会组成一片森林的。”夏桐说。他当然知道,这片“森林”目前还只能匍匐在地底下,而且必须本能地把自己完全掩藏起来,越深越好。
存在 一个庞大而隐秘的人群
5年前,夏桐在认识和熟悉互联网之前,根本没有想到原来有那么多人竟然和自己一样。他们是男人,却一点都不喜欢女人。
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夏桐更愿意接受“同志”的称呼,这也是中国同性恋者普遍认可的一个称呼,其中男性也称“Gay”,女性称“Lesbian(中文译为“拉拉”)”。2004年底,卫生部多年来首度打破沉默,公布了一个估算数据: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同性恋者有500万至1000万人。但著名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马丁奖获得者张北川教授,则根据持续多年的调查认为,中国内地15岁到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000万,其中男性2000万,女性1000万。他们广泛存在于城市、农村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是张北川教授多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地点之一。它是除了北京、广州、成都、重庆等几个城市之外,全国“同性恋”人群聚集较多的城市。淳厚的民风,独特的文化内涵,加之高校林立,年轻人聚集,西安因此吸引了众多异乡客在此驻足。那些在家乡遭受情伤,或者因为暴露“同性恋”身份而不得不自我放逐的人,愿意在这里愈合他们的伤口,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的世界
挣扎 一位男“同志”的成长
在我们接触的众多“同志”中,夏桐的故事并不特别。然而,接近30岁的尴尬年龄,让他成为这个人群中的一个典型。
比他年龄大的,因为受不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绝大多数都已走进了婚姻“堡垒”,虽然终其一生很难从婚姻中获取幸福,但有婚姻的外衣作为屏障,至少可以延续一种正常的生活。而比他年龄小的“gay”,大多才20岁出头,因为网络的普及和交往的频繁,他们较早地发现并确定了自己的性取向。他们中的许多人,乐于接受自己的“同志”身份,积极地去追逐爱与被爱。而将近而立之年的夏桐,则异常沉重。他渴望拥有一份稳定的真爱,但又不愿意坦然承认和接纳自己,试图有一天走上普通人的生活轨道。也因此,他徘徊在婚姻的边缘,在感情的挫折和社会压力之下,希望能躲进婚姻里去,虽然知道那才是“真正心灵痛苦的开始”。他的故事,代表了许多同性恋者的成长与挣扎。
记者:小时候发现自己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吗?
夏桐:我家在一座小城里,妈妈在我8岁时瘫痪了,我一直承担着照顾妈妈的责任,父亲脾气暴躁,我虽然是惟一的儿子,却常遭到父亲的痛打。只有奶奶最疼我,这一切让我特别独立、固执而又敏感。也许这也是一点关联,但我想不是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天生的吧,我基本上对女孩子没有感兴趣过。
记者:为什么会来到西安?
夏桐:来西安时,我的心情正是灰暗的时候,做生意赔了,母亲刚刚去世,女朋友也离开了我,我等于是逃到西安来的。到这里后,我报了××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来圆自己的求学梦。
记者:喜欢过女孩吗?初恋是什么时候?
夏桐:十八岁左右,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她对我特别好,可能是这让我感到温暖和安慰吧,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她离开了我这个穷小子,找了个有钱人,我当时也难过,但很快就过去了,主要还是自尊心接受不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的初恋吧,因为我一直没有那种爱的感受,我从没有强烈地思念过她,和她在一起,也没有甜蜜的感觉。
记者:那真正的初恋呢?
夏桐:应该是我在西安求学时那个上铺的舍友吧。他是学理科的研究生,我俩很投缘,他知道了我过去的经历,一直鼓励我要振作起来,还常在学业上指点和帮助我。他很勤奋,每晚做实验都是最后一个才走,他的刻苦也感染了我。他爱弹吉他,我就是他的忠实听众。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几天不见,心里就不踏实,感情和心灵上开始特别依赖他。
记者:那时对自己的性取向明确吗?
夏桐:那时是纯洁的朋友交往,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同志”倾向。但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发呆,他出差十多天,我特别牵挂和想念他。有一次,他的牛仔裤破开了一条缝,看他笨手笨脚地缝着,我抢过他的针线,麻利地缝起来。这时正好对面宿舍的一个舍友过来串门,就开玩笑地问我:“阿桐,你为什么给他缝裤子啊?”我一下愣住了,一时不知道怎么说,就脱口而出:“我爱他。”结果他们哄然大笑,好朋友的脸立刻红了起来,我的脸也红了。两个大男人说这些话实在不恰当吧,可我当时真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和喜欢。
记者:向他表白你的感情

